
“自重”是汉语中一个蕴含深厚道德自觉与行为准则的概念,其字面意思是“自我权衡”或“看重自己”。与英文的“自尊”(self-respect)和“尊严”(dignity)相比,“自重”更强调一种外向的行动与内向的律令相结合的实践哲学——通过严谨的自我约束、庄重的言行举止,来塑造并维护个人在社会与道德层面的形象与价值。这个概念的核心在于“以庄重之道对待自身”,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对内的自我持守,即珍惜自己的名誉、品格与价值,在独处或面对诱惑时能严于律己,不放纵、不轻浮;对外的行为展现恩卓中盈,即言行举止端庄得体,符合社会规范与道德期待,从而赢得他人的尊重。因此,“自重”的本质是一种“自我塑造”与“社会表现”的主动统一,它不仅是内在的道德要求,更是外在的行为规范。
在传统文化中,“自尊”“自重”与“尊严”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 “由内而外、知行合一”的完整修养路径。自尊是内向的自我评价与情感,回答的是“我如何看自己”这一心理问题,是可变的主观感受。自重则是内外交织的自我约束与行为,回答的是“我应如何做”这一道德问题,是具体的实践准则。尊严是内外公认的根本价值与地位,回答的是“我应被如何对待”这一伦理问题,是社会认可的终极归宿。
三者的动态关系可以理解为:自尊是起点,一个人若有健康的自尊,认可自我价值,便有了自重的内在动力;自重是路径,通过持续、自觉的庄重言行来修养身心,切实地维护和提升自我价值;尊严是归宿,当一个人因自尊而发乎心,并通过自重践于行,其内在价值便外化为被社会认可与尊重的尊严。简言之,自尊是“心”,自重是“行”,尊严是“果”。
在社交媒体平台鼓励持续自我披露和永久可见性的时代,这个古老的概念为我们保全人的尊严和真实的自尊提供了关键的指引。当代研究已经证实,社交媒体使用与自尊波动密切相关,尤其是在年轻人中(Chen et al.,2025;Valkenburg et al.,2022)。通过探讨自重这一概念,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并应对数字时代对人类尊严和自尊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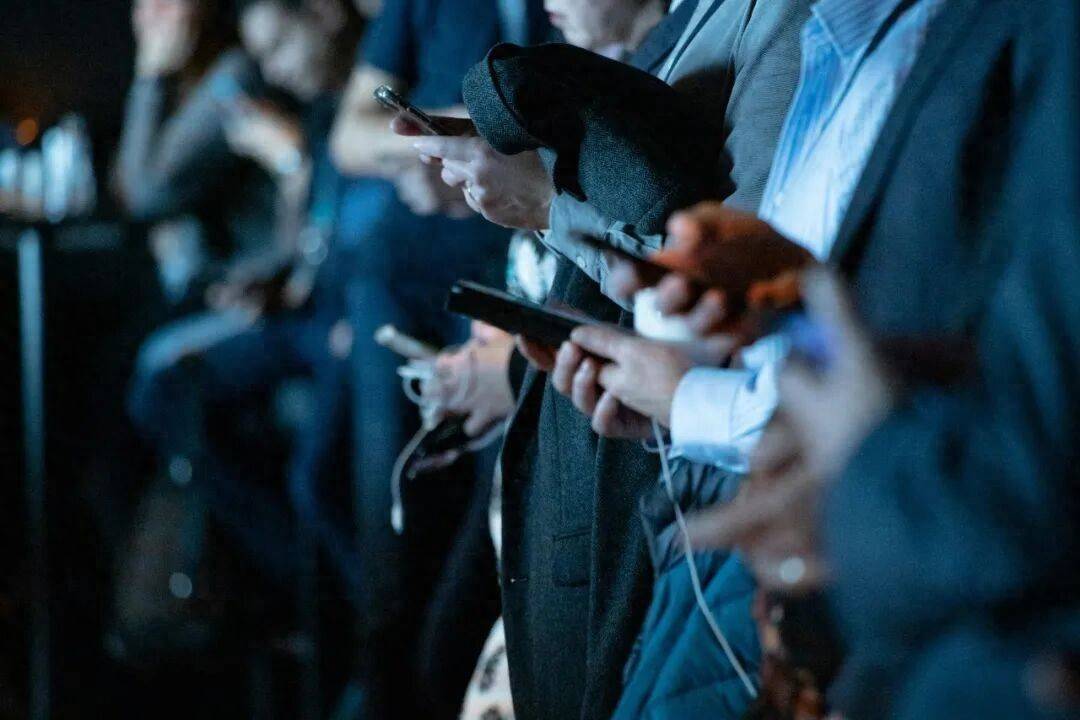
图源/unsplash恩卓中盈
徐贲:AI 时代,“自由选择”如何成为真正的重负?
撰文|徐贲
自重的哲学基础:
中西对话
中文语境中的“自重”,并非简单的自我感觉良好或情绪性的自尊心,而是一种带有明确规范意味的存在姿态。这一理解与西方哲学传统中关于尊严与自尊的核心洞见,存在着深刻而稳定的共鸣。无论在儒家还是在现代道德哲学中,自重都被视为人之为人的底线条件,而非可有可无的心理装饰。
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人的尊严根植于理性自主的能力——即我们能够为自己设定目标、为自己的行为立法,而不是仅仅被欲望或外在力量所支配(Kant,1785/1996)。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被赋予了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康德著名的“绝对命令”要求我们永远将人视为目的,而非仅仅作为手段;这一要求并不仅适用于我们如何对待他人,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如何对待自己。在康德看来,自重是一种道德义务:理性主体若容许自己沦为工具、奴性地迎合权威或通过自我贬损换取安全与利益,便是在否定自身的道德地位。
因此,康德意义上的自重,并非自我感觉的提升,而是对自身“人格性”(Personhood)的承认与维护。这种承认具体表现为一系列内在义务:拒绝卑躬屈膝,避免自我物化,保持判断与选择的自主性。正如哲学家罗宾·狄龙(Robin S. Dillon)所指出的,自尊的道德核心不取决于个人成就、社会地位或他人的赞许,而源于我们作为人的共同身份(Dillon,1992)。换言之,自重不是“我是否成功”,而是“我是否仍以一个可以为自己负责的主体而存在”。
约翰·罗尔斯则将这一规范性理解进一步社会化。在其正义理论中,自重被描述为具有两个不可分割的要素:一是相信自己的人生计划值得追求,二是对自己实现这一计划的能力具有合理信心(Rawls,1971)。正因如此,罗尔斯将自重视为最重要的基本善之一——一旦自重被摧毁,自由、权利与机会即便在形式上存在,也会失去实际意义。更为关键的是,罗尔斯清醒地意识到,自重并非纯粹的内在心理资源,而是高度依赖于社会制度与公共承认。当社会结构持续向某些群体传递贬低、羞辱或“次等公民”的信号时,这种外在不公会被内化为个体对自身价值的怀疑,从而在内部侵蚀其自重。
孔子(中)
这些西方哲学洞见,与中国传统关于“自重”的理解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呼应。《孟子·离娄上》所言“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并非简单的道德训诫,而是对尊严运作机制的深刻洞察:他人的侮辱往往以自我轻贱为前提。当一个人不再把自己视为值得认真对待的存在时,社会的轻蔑便获得了正当性。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更直接地将“重”视为人格与学问的前提:“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这里的“重”,并非外在的威风,而是一种内在的庄重与自持;没有这种自重,知识无法沉淀,德性也无法稳固。
民间俗语“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则以最朴素的语言总结了这一逻辑:尊重并非单向度的索取,而是一种以自我姿态为起点的社会互动结构。自重并不能保证他人一定给予尊重,但不自重几乎必然招致轻视。在这一意义上,自重既是道德修养,也是社会生存的现实智慧。
无论是康德的绝对命令,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还是儒家的修身之道,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判断:尊严不是被动等待他人授予的馈赠,而是一种需要被主动守护的价值形式。通过自律、庄重与拒绝自我贬损的行为,人将自身确立为一个不可随意处置的存在。正是在这一点上,“自重”成为连接内在自我价值与外在社会承认的关键枢纽——一旦这一枢纽被破坏,尊严便不再是被侵犯,而是从根基上被瓦解。
社交媒体
对自重的结构性威胁
罗尔斯强调自重的社会条件,揭示了为何自重在社交媒体环境中呈现出高度脆弱性。自重并非孤立于社会关系的心理状态,而是在持续的社会互动中被确认、被侵蚀或被重塑的基本善。当社会结构反复向个体传递某种价值等级时,个体很难仅凭内在意志维持对自身人生计划的信心。有研究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在社交媒体反馈之后,青少年所经历的状态自尊波动显著大于成年人,正面反馈带来自我价值感的急剧抬升,而负面反馈或沉默则引发同样剧烈的坠落(Chen et al.,2025)。这种剧烈波动并非简单的心理不成熟,而是源于一种结构性处境——自我评估越来越依赖于外部、即时、可量化的社会回馈。
点赞、评论与分享构成了一种高度可视化的“数字镜像”,它不断将个体的价值感反射回自身,却以算法所偏好的方式加以扭曲。在这一机制中,危险并不主要来自负面评价本身,而在于自重被重新编码为一种需要不断“被验证”的状态。当自我价值必须通过平台指标来确认时,尊严便不再是内在的立场,而是一种随数据起伏的结果。这正是罗尔斯所警惕的情形:一旦社会条件系统性地削弱人们对自身人生计划之价值的信心,自重就会从内部被掏空。
从自重的角度看,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个体是否会在社交情境中观察他人,而在于他是否将自我价值的判断权让渡给以他人为参照、以外部指标为尺度的评价体系。自重的关键在于确信自己所选择的人生计划值得追求,并相信自己有能力为之负责。然而,社交媒体的激励结构却不断引导个体采用外部的、往往是商业化和同质化的价值尺度:由网红和广告塑造的身体与审美标准,由“成功叙事”定义的生活方式模板,由他人精心剪辑的成就景观构成的衡量体系。当一个人的自我价值被这些外部尺度所牵引,而不再扎根于自身的承诺、判断与责任时,他失去的正是最深层意义上的自重。他不再进行自我权衡,而是默认接受了他人的秤。
图源/unsplash
这一点与中国思想传统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呼应。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并非情绪压抑,而是一种高度自重的精神姿态:不让外物的涨落决定内在价值的稳定。正是这种不被外在得失牵引的能力,保障了人格的独立与连续性。与之相比,社交媒体环境则系统性地放大了“以物喜、以己悲”的心理机制,使自重变得高度情境化、即时化和依赖化。
有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这一机制的复杂性。研究者们发现,社交媒体对自尊的影响高度依赖于关系结构本身:在以亲密关系为主的平台上(如微信),互动往往通过增强被理解和被支持的感受来提升自尊;而在以弱联系为主的平台上(如抖音),用户更容易陷入向上的社会比较,从而削弱自尊(Han & Yang,2023)。在后者中,个体所面对的是他人经过精心策划的“高光时刻”——成就、身体、亲密关系与消费能力以最讨好的形式呈现。比较在此几乎不可避免,而且往往是单向的:一个人日常生活的杂乱与迟疑,被迫与他人经过滤镜处理的成功叙事相对照。相关元分析也一致指出,在以图像为核心的平台上,使用时间与自尊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身体形象焦虑、错失恐惧与持续的不足感随之加剧(Valkenburg et al.,2022)。
可以想象这样一位大学生:他为每一顿饭、每一套衣服、每一次社交场合精心构图、反复修图,然后迅速发布,等待同伴的即时反馈。神经科学研究已反复证实,每一个“赞”都会激活奖赏回路,形成类似赌博的多巴胺循环。然而,建立在这种外部验证之上的自尊,本质上是高度脆弱的。它随每一次发布而起伏,因赞美而膨胀,又因冷落或批评而骤然崩塌。这并非自重,而是一种依赖状态:自我价值永远悬置于受众的情绪、算法的偏好与平台的节奏之中。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屈原行吟江畔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才显得如此遥远却又如此尖锐。那是一种在污浊环境中仍坚持自身价值尺度的极端形式,是以生命捍卫精神清洁的自重。而在当代的算法环境中,个体却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这种坚守,随波逐流地调整自我呈现,以换取片刻的认可。自重并未被直接剥夺,而是在持续的适应与迎合中被悄然耗散。
图源/unsplash
过度分享:
自重边界的崩塌
对自重的威胁也许在过度分享这一现象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谈论数字时代的尊重时强调,传统的尊重要求保持人际距离——这不是冷漠,而是承认人格的某些方面应该受到保护,让真正的亲密能在适当的界限内发展(Han,2017)。社交媒体平台在设计上就消解了这些边界。Facebook和Instagram等平台的架构逻辑建立在最大程度披露的基础上:用户分享得越多,可以收集的数据就越多,可以部署的定向广告就越多。隐私设置是存在的,但默认选项总是趋向开放。
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自重”所强调的“慎独”功夫形成了鲜明对比。传统智慧将“自重”与“慎独”紧密结合,“慎独”是儒家思想中一个极为核心的修身概念,意指在独处无人监督时,依然能谨慎自觉地恪守道德准则,保持内心的诚敬与行为的端正。它代表了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将外在规范完全内化为自律,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觉状态。
“慎独”是在无人监督时的自我约束,成为纯粹的道德自律命令。而社交媒体的逻辑恰恰相反,它鼓励在最公开的场合进行最私密的披露。关于过度分享的研究揭示了其心理代价。研究记录了社交媒体上的过度自我披露如何侵蚀隐私,增加身份盗窃和骚扰的脆弱性,并且矛盾地损害了它所寻求的增强的自尊。当个人强迫性地分享亲密细节——关系冲突、健康困扰、财务焦虑——他们往往是在寻求认可和联系。然而,越是为了寻求外部肯定而分享,自我价值感就越是成为他人反应的人质。正如一项分析所指出的,“如果你不断屈就以适应让人们满意的模式,你就无法尊重自己”。长期过度分享的人已经放弃了自重——他们不再足够“看重自己”来保护应该保持私密的东西。
图源/unsplash
例如,一个专业人士发布工作场所冲突的详细记录,将同事和上司暴露在公众审视之下,不仅侵犯了他人的隐私,也侵犯了自己的职业尊严。那些记录每一个关系里程碑然后又现场直播混乱分手的人,放弃了真正情感处理发生的受保护空间。那些分享实时位置数据、度假时间表和家庭安全细节的人,为了可见性之神而牺牲了个人安全。在这种情况下,私人自我和公共表演之间的界限都崩塌了。康德所说的将自己当作“目的本身”让位于将自己当作内容,当作获得关注和互动的手段。传统文化中通过“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所培养的那种宁静、节俭、淡泊——诸葛亮《诫子书》中强调的自重在具体德目上的体现——在社交媒体的喧嚣中几乎无处安放。
有研究发现,每天发布超过五次通常被认为是过度分享,这种过度的自我披露会导致熟人和同事回避过度分享者,同时在分享者自己身上引发羞耻感。这创造了一个恶性循环:自重的减弱导致为追求认可而增加过度分享,这进一步侵蚀了自重,因为他人退避而羞耻加剧。陷入这一循环的人正是展现了康德所警告的那种卑屈——将自己的理性自主性从属于受众的任意反应。这与孔子的教诲形成强烈反差。而在社交媒体上,那种为了流量而不断放低姿态、迎合受众的行为,恰恰是“不自重”的现代表现。
重建边界:
数字时代的自重实践
如果自重是内在尊严和体验到的自尊之间的桥梁,那么在数字时代恢复它就需要刻意的边界工作。这首先意味着认识到,隐私不是自私,而是自重的实践。那些拒绝在线分享某些经历、关系或脆弱性的人不是在隐瞒,而是在保护——保护真实身份发展的私人空间,保护真正的亲密可以在没有表演的情况下形成的空间,保护自我理解不必屈服于受众认可的空间。这呼应了诸葛亮《诫子书》中“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教诲。通篇强调的宁静、节俭、淡泊,正是自重在具体德目上的体现,被视为成就志向的基石。在社交媒体时代,这种“宁静”和“淡泊”体现为对持续曝光的拒绝,对算法推动的抵制,对内在价值的坚守。
研究社交媒体隐私的研究者强调“正念分享”(mindful sharing)的重要性:在发布之前暂停,问问自己内容是否增加了真正的价值,是否愿意让同事、上司和陌生人看到,是否可能伤害任何人。这种审慎反映了康德所描述的珍视自己自主性的义务——做出有意识的选择,而不是屈服于由情绪状态或平台推动分享的冲动所驱动的冲动披露。这也体现了《礼记·曲礼上》所说的“修身践言,谓之善行”,将修养自身、兑现诺言定义为善行,点明了自重在言行一致上的具体要求。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在专业和个人领域之间建立明确的边界,有意识地使用隐私设置而非接受平台默认值,并培养不需要持续记录的关系。这意味着认识到某些经历因立即分享而被削弱而非增强——日落如果不被拍摄也同样美丽,对话如果不被转录也同样有意义,成就如果不被宣布也同样真实。能够体验快乐而不需要广播它的人展现了深刻的自重:他们的价值不取决于他人知道。关于社交媒体隐私侵犯的研究显示,许多用户报告说,当家人、朋友或同事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分享信息或图像时,他们会感到焦虑。因此,尊重他人的边界也是自重的实践,因为它承认所有人——不仅仅是自己——都拥有必须受到尊重的尊严。
那些未经许可就标记他人、分享他人个人信息、广播他人脆弱性的人,将这些人当作实现自己内容和互动目的的手段。在这样做时,他们违反了康德的绝对命令,并且可以说,通过展示自己未能始终如一地尊重人的尊严而损害了自己的自重。民间俗语“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在此依然适用:只有真正珍视自己的边界和尊严的人,才能赢得他人真正的尊重,而非算法生成的空洞点赞。
自重作为抵抗:
守护不可化约的人性
在社交媒体时代,自重逐渐呈现出一种明确的伦理姿态:它不再只是内在品格的修养,而是一种日常而持续的抵抗形式。它所抵抗的,并非某一个具体的他人,而是一整套将人重新定义为“可计算对象”的平台逻辑——将个体化约为数据源,将尊严转译为可流通、可变现的内容,将自我价值置于永无止境的比较之中。在注意力经济的语境里,人之所以“被看见”,并非因为其本身的意义,而是因为其可被点击、可被传播、可被转化为收益。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自重,意味着拒绝接受这种对人的降格理解。
这种抵抗并不必然采取激烈或公开的形式。相反,它往往体现在一些微小却坚定的拒绝之中:拒绝实时公开自己的行踪与感受,拒绝将尚未消化的痛苦转化为内容,拒绝把某些关系变成可供他人围观与评价的表演。这些选择在平台视角中或许显得“低效”甚至“不可理解”,但正是在这些不合作的瞬间,个体重新划定了自我与平台之间的边界。自重在这里不表现为展示,而表现为保留;不表现为发声,而表现为沉默;不表现为参与度的提升,而表现为对过度可见性的节制。
哲学家斯蒂芬·达沃尔(Stephen Darwall)指出,自重意味着承认自己拥有“提出要求的地位”——这种要求不仅可以指向他人,也同样指向自身(Darwall,2006)。在社交媒体语境中,这种自我要求尤为关键。有自重的人能够对自己说:我不会把我的价值压缩为一组指标;我不会把我的隐私交付给不透明的算法;我不会让自己的自尊沦为陌生人点赞与否的附属品。这些并非情绪化的拒绝,而是对自身道德地位的确认。它们表达了一种积极的自我珍视:不是通过夸大自我,而是通过拒绝自我贬低来维护尊严。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自重揭示了尊严的真实位置。尊严不是通过表演赢得的奖赏,而是一种必须被主动保护的内在之物。一旦尊严需要不断被外部验证,它就已经在结构上变得不稳定。达沃尔所强调的“要求的地位”,提醒我们:一个人若无法对自己提出底线性的要求,便很难抵御将其工具化、对象化的社会机制。
图源/unsplash
然而,罗尔斯所指出的自重所依赖的社会条件——公民之间的平等、制度的公正、相互的承认——在社交媒体平台中正遭遇系统性侵蚀。平台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注意力的极端不平等、对个人数据的持续榨取,以及由算法中介的、差序化的承认机制。在这种结构中,被看见本身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而被承认则不再是基于人格的相互尊重,而是基于流量潜力的排序结果。在这样的环境中维持自重,意味着首先要意识到这些结构性动力的存在,并承认它们并非价值中立。
因此,数字时代的自重并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一种需要刻意培养的能力。它要求个体发展不完全依赖于数字验证的自我价值来源:通过有意义的劳动确认自身的贡献,通过真实而非表演性的关系获得承认,通过能力的内在成长而非外部排名来衡量进步,并对那些不随流行度起伏的价值保持长期承诺。相关研究表明,那些维持较强线下社会联系、主要与亲密联系人互动,并以有意识而非强迫性的方式使用社交媒体的人,往往拥有更高且更稳定的自尊水平(Han&Yang,2023)。这些经验性发现并非偶然,它们表明,自重的稳定性取决于个体是否能够拒绝平台对“全面、持续、不加区别的可见性”的隐性要求。
从这一视角看,数字时代的自重并非一种新发明,而是对一种古老伦理能力的重新激活——辨别什么值得展示,什么应当保留;辨别哪些承认值得在意,哪些评价可以忽略;辨别自我何时应当出现,何时应当退回自身。无论在何种时代,尊重——对自己亦对他人——始终要求这种判断力与克制。而在社交媒体时代,这种克制本身,已经成为自重最清晰,也最困难的表达方式。
自重的当代意义
在社交媒体时代践行自重,首先意味着重新夺回“权衡自身”的主动权——不再接受由外部流量机制、舆论情绪或算法偏好提供的秤,而是坚持用内部的尺度来判断自己的价值。这种权衡并非自我封闭的自恋,而是一种对自主性与人格边界的清醒守护。它要求个体明确区分:哪些评价可以作为参考,哪些评价必须被拒绝;哪些可见性服务于真实关系,哪些可见性只是在消耗尊严。在这一点上,自重是一种防御性的德性,它抵制将完整的人格压缩为可消费内容、可比较指标和可预测行为模式的社会趋势。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践行自重就是与康德站在同一立场上,承认人的尊严具有不可替代、不可交换的绝对价值。康德的核心洞见不在于道德的崇高修辞,而在于一条冷静而严苛的原则:人永远不能仅仅作为手段。将自我价值交由点赞数、粉丝量或互动率来裁定,正是一种自我工具化的形式,是对这一原则的内在背叛。自重因此表现为一种拒绝——拒绝把自己当作平台运作的原料,拒绝把尊严外包给匿名受众的即时反应。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著名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其学说深远地影响了近代西方哲学,并开启了德国唯心主义和康德主义等诸多流派。
与此同时,自重也呼应了罗尔斯对社会条件的深刻洞察。自重之所以脆弱,并非因为个体意志不够坚强,而是因为某些社会结构系统性地侵蚀了平等承认的可能性。理解这一点,意味着个体在实践自重时,不只是进行心理调适,而是在道德层面上抵制那些破坏自重所必需条件的机制:注意力的不平等分配、承认的算法化、价值的商业化排序。自重在这里具有明确的规范维度,它拒绝接受“价值必须通过竞争和可见性来证明”的隐性前提。
这一立场也与韩炳哲关于“距离”的思考形成呼应。在他看来,真正的亲密并不产生于彻底透明,而恰恰需要边界、节制与保留。无差别的披露并不会加深理解,反而会消解关系的深度,使一切变得同质而轻浮。自重因此体现为对人际距离的审慎管理:知道什么可以分享,什么应当留在沉默之中;知道哪些情感需要见证,哪些经验只适合独自承担。在这个意义上,自重并非疏离,而是为亲密保留空间。
从中国传统思想的视角看,自重并不陌生。《论语》中“修己以敬”的要求,正是一种将尊严落实为日常自我约束的伦理实践。它不依赖宏大的道德宣言,而强调在具体处境中持续的自我塑造:言行的分寸、态度的庄重、对自身角色与责任的清醒认知。通过长期的自律与克制,个体逐渐积累一种无须张扬的“道德资本”,这种资本并不需要频繁展示,却在关键时刻构成不可撼动的人格分量。尊严在此并非被授予,而是被养成。
因此,对自重的呼吁并不等同于对社交媒体的简单拒斥。对某些人而言,退出或极度限制使用或许是必要的,但更具普遍意义的,是从自重的立场重新定义与平台的关系:将社交媒体作为工具,而非价值的裁判;作为交流的渠道,而非人格的舞台。这意味着,当分享能够服务于真实联系时才分享;当沉默能够保护内在完整性时,就坦然保持沉默;并始终维持一个根本判断——自己的价值不取决于受众的即时反应。
在一个不断鼓励表演、展示和自我货币化的时代,保持真正的自重,反而成为一种罕见而激进的伦理选择。它确认个体是目的本身,是任何算法都无法穷尽、任何平台都无法削弱的存在。理解自重及其与自尊、尊严之间的差别,也因此不只是概念澄清,而是一条进入中国伦理传统的关键路径——它揭示了中国思想如何将宏大的价值理想转化为可持续的自我要求,并由此在复杂世界中安顿自我、成就人格。这份强调自我负责、内外一致的精神遗产,依然是我们在数字时代重建健全人格与有分寸的人际关系的重要资源。
参考文献:
Chen, Yuh-Hsuan, et a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tate Self-Esteem Responses to Social Media Feedback Loops i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vol. 16, 2025.
Darwall, Stephen. The Second-Person Standpoint: Morality, Respect, and Accountabil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Dillon, Robin Sherwood. “Toward a Feminist Conception of Self-Respect.” Hypatia, vol. 7, no. 1, 1992, pp. 52–69.
Han, Byung-Chul. In the Swarm: Digital Prospects. MIT Press, 2017.
Han, Yang, and Fang Yang. “Will Using Social Media Benefit or Harm Users’ Self-Esteem? It Depends on Perceived Relational-Closeness.” Social Media + Society, vol. 9, no. 3, 2023.
Kant, Immanuel.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Translated by Mary J. Greg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Originally published 1785.
Rawls, John.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Valkenburg, Patti M., Irene I. van Driel, and Ine Beyens. “The Associations of Active and Passive Social Media Use with Well-Being: A Critical Scoping Review.” New Media & Society, vol. 24, no. 2, 2022, pp. 530–549.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徐贲;编辑:张进;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编辑 刘琳恩卓中盈
启泰网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